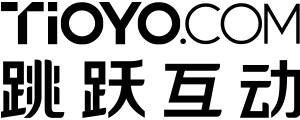作者:DANIELLE SACKS 翻译:李乙枫
新型公司越来越多运用数字科技来完成业务,传统广告公司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MediaMath,DataXu和X+1公司正在竞相提供数字化媒介购买平台;Buildbrand.com把品牌规划简化为一套运算,5分钟就能产生几套符合需求的品牌logo;Lotame公司的观众数据管理,能够追踪广告投入的每一分钱是否花得正确有效。Facebook、Foursquare之类的互联网明星,干脆直接和品牌合作,广告公司只有看的份儿。
20位创意总监
曼哈顿下东区的一所百年老宅里,来自全美的20位创意总监、策划人员、媒体策略和AE们正伏案挠首。他们被要求在一张海报大小的白纸上,写下对自己职业现状、谋生能力、未来前途的种种担忧和焦虑。没错,他们有很多的担忧和焦虑,因为他们身处广告行业。
这所三层楼的房子在中国城边上,里面是一家叫Hyper Island的瑞典广告名校。Hyper Island校本部在波罗的海上的一座古老监狱里,以拥有和广告业最让人垂涎的数码时代天才而著称,他们的宗旨是“数码营销无边界”。
Hyper Island于去年夏天开设了这家纽约分部。它和其它进驻纽约的外国公司一样,有很大野心:把麦迪孙大道上的“土著”都拽入21世纪。对于它来说,瑞典校本部的学生们都是“数码原住民”,而这些纽约的老头老太都是刚刚弄懂新时代运作方式的“数码移民”。“移民”们现正聚集在此,接受为期3天的浸泡式培训,主题“数码科技对广告行业的革命性冲击”。一名课程教师如此解释:“数码移民的典型行为,就是给别人发了一封email之后,还要打电话过去确认。”
接受培训的人平均年龄38岁,大多都在广告公司工作10年以上。以往,这个数字代表着丰富的资历,而现在,它却很可能是一种负担或障碍。这些人都清醒意识到,现在程序编码比广告文案更受青睐,简历里如包含Xbox或Google的相关工作经历,一定比BBDO或精信的一个成功案例要抢手得多。
培训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正视自己的“问题”。房间里布满了让人放松的宜家的桌椅和瑞典小甜饼,20位广告人被要求把自己有关数码时代的种种不安和忧虑“放到台面上”。最终,每个人都趴在桌上写写画画,然后聚成一圈(一种给人安全感的空间结构),诉说自己的问题。
“我总是有莫名的恐惧感,每次遇到有关数码类的问题,都觉得很被动,很茫然。”
“我每次碰到这种问题都觉得是个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觉得头上有成百上千个棒球从天上掉下来,我站在中间,不知道应该接哪个。”
“我本来在一家国际公司工作,现在辞掉了。。。好吧,我是被辞掉了。”
“我觉得数码世界有一扇敞开的大门,但我连怎样进去都不懂。”
“这种消除创意和美术分工的‘团队合作’,对我来说无比困难。”
接下来的72小时,对于这些广告人来说要么是一种折磨,要么是一堂新时代营销入门。他们被告知,创意团队如今应该更多地向即兴演员学习,只有“创造故事”而不是“讲述故事”,才能迅速抓住现在越来越难以捉摸的观众。营销应该是“有效的”而不是“广而告之的”,所以创意人的角色应该更像是某种全新产品的开发人员,而不是娱乐节目演员。从前,广告活动都会推出一些光鲜亮丽、打动人心的完美的概念,观众坐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等待着被它俘获。现在,数码营销是渐进的、实验的、不断改进的(参见互联网中的各种“测试版”),而且永远、永远没有“完美版本”。课程教师这样说道,“数码变革会颠覆你们公司的盈利方式、雇佣方式和报价方式。你们必须扭转一下自己的DNA,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课程中还有教你弱化“自我”的环节。而且在整个培训里,老师们不断提醒这些道上“新手”,现在学到的这些全新观念,也会很快被更先进的观念颠覆掉。
[ 困局 ](上)
广告实践已经像琥珀中的甲虫,在过往半个世纪里都没发生多大变化。1960年以前,广告人就像独居者一样活着。文案人员绞尽脑汁想出一句精彩的文案,然后交给美术指导,转化成插图或照片。后来创意总监Bill Bernbach(也就是DDB里面的B)让字匠和画家搭档,他认为这样能产生更有创意的灵感火花。这在行业中算是一场革新运动,将“做广告”从很cheap的推销行为上升为一种艺术行为。
如今,广告运作越来越像流水作业。客户(他的目标是从他的产品中提炼出唯一的关键词)付钱给AE(他的工作是引诱客户付钱,而且要开心地付钱),AE就下brief给品牌策划(他的调研将揭示伟大的消费者洞察),他又下brief给媒介策划(他去决定广告是通过广播,平面,户外,直邮,还是tvc进行)。文案和美指接管工作(比如弄出一个30秒tvc故事版),给制作人(他的工作是和导演、剪辑师合作拍摄剪辑出最终的tvc)。通过媒体购买人员(他的工作是给媒体的人陪饭陪酒,以获得更低的tvc、广播时段或版面价格)的努力,广告最终新鲜出炉,投放到上述5种媒介。TVC是媒介中的大头,因为它不仅能够接触到最多的受众,而且还是最贵的媒介——客户能花的钱越多,广告公司能赚的钱也就越多。
以上都是忆当年了。
近年,由于互联网对各行业的冲击、经济衰退、商业合作盲点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流水线模式也从经济、组织、文化意义慢慢瓦解。广告行业美好的2007年,已经像1962年的威士忌热潮一样一去不返。Marsteller广告公司前任CEO Andy Nibley抱怨道:“它又来了。一开始是新闻业,然后是音乐界,现在轮到广告。跟我工作有关的每一个行业,都要被数字技术革命一次。”
不过,多亏互联网和数码科技,广告公司发现自己仍然能够帮助客户实现终极梦想:在正确的时机、向正确的群体、传达正确的信息。然而他们还是面临非常复杂而严峻的考验,因为毕竟数码渠道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渠道,而是个n多种媒介的总和。曾任花旗集团和Macy’s广告业务总管的Brad Jakeman说,搜索、地理定位、iPad、移动应用等大量新平台的产生,造成广告媒介预算严重分散、消费者注意力严重分散。“真的很讽刺,我们和消费者接触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多,但有效接触也前所未有地难,”现任Activision游戏公司CCO的Jakeman说道。大众营销之死,也是懒惰营销之死。现在,广告公司的工作以几何倍数增多,他们也正在对此习以为常。试想当年W+K 于48小时内在YouTube投放的200条Old Spice香水短片.“工作变多了,钱赚少了,这是个悖论,”波士顿Modernista广告公司老总说。
而且,互联网把原本单向可控的信息,变成了和所有人的即时互动。“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和广告持平,甚至向广告发出挑战。”IPG旗下麦肯世界集团CEO Nick Brien说。他认为,像Engadget和Yelp!之类的网站,既可以成就一个产品,也完全可以毁掉一个产品。营销人员的出路,不再是在媒介上付费进行信息传播,而是通过让消费者在YouTube、Groupon、Twitter上,像转发自己bb的可爱照片一样狂热地转发对他们有益的信息,免费“挣”得媒体。Kirshenbaum Bond Senecal + Partners创始人之一、一年后再次创业的Jon Bond说:“在未来,营销就像XXOO,只有失败的人才需要付钱购买,你懂的。”然而另一方面,市场完全开放透明也有弊端,营销者如果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就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硬生生赋予某个品牌它所不具有的气质,这种做法现在行不通。
所以,广告主发现自己越来越迷茫。在预算紧缩的条件下,营销高管们找不到精准的应对措施。他们既不认为那些来自“旧世界”的大广告公司有办法指点迷津,又不敢轻信那些出身“新世界”的新公司。Jakeman说:“做广告是全美国最不靠谱的工作,过失永远都归我们,功劳永远都归别人。”他说,现在首席营销官的平均任职时间是22个月。
当广告主身陷数字时代困境,广告公司的角色面临挑战。很多企业的营销官开始摈弃那种长期、固定的代理模式,这是很多全案代理公司的噩耗。去年,百事旗下的SoBe品牌市场总监Angelique Krembs在完成了新的一轮代理公司评审之后,就决定将所有全案代理公司拒之门外,只跟擅长数字营销、公关、促销的小公司合作。Krembs说:“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和哪个公司合作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我们正在尝试超越传统,赶上时代的步伐。我们意识到,单独一个公司并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广告需求,单个媒介也不能完成我们所有的传播需求。”现在,在数码传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营销高管大多会认同这种看法(接受过宝洁或General Mills洗脑的传统传播人士则不然)。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西尔斯公司新聘的营销总管David Friedman,就是从数字广告公司Razorfish请来的。
[ 困局 ](下)
广告公司不但要承受客户方面的压力,还要被一群新生的竞争对手围攻。技术公司已经把传统广告流水线作业模式中仅存的一点“艺术”彻底商品化,生产广告不再是一件昂贵、耗费人力物力的工作,如今2千美元一台的摄录机,拍出的画质已经能够满足广告的需求。像埃森哲、沙宾特之类的咨询公司,也已经给自己贴上“数字公司”标签。微软、IBM、谷歌等技术巨人,不断抛出创新而实用的数字化工具,代替咨询公司内部的传统分析模式,结果更为精准,而且还能将每一项因素都量化。作为业内评价最分化、亦敌亦友的谷歌老大,在为几家咨询公司提供分析和策划工具的同时,也在帮他们实现媒体购买自动化。BMO Capital Markets一名负责广告和营销业务的分析师说:“互联网广告拥有无限多的投放空间,所以你很难再让分析师进行媒体策划了,现在我们都用软件来搞定。”
新型公司越来越多运用数字科技来完成业务,传统广告公司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MediaMath,DataXu和X+1公司正在竞相提供数字化媒介购买平台;Buildbrand.com把品牌规划简化为一套运算,5分钟就能产生几套符合需求的品牌logo;Lotame公司的观众数据管理,能够追踪广告投入的每一分钱是否花得正确有效。Facebook、Foursquare之类的互联网明星,干脆直接和品牌合作,广告公司只有看的份儿。更大的打击来自那些“背弃”了自己原本公司的人。John Winsor离开CP+B后,在科罗拉多创立了Victors & Spoils,公司里没有员工,靠“群众外包”(现今广告界最受鄙视的方式)完成业务。自开业以来,就相继吸引到General Mills,Oakley,维珍美国、Harley-Davidson的营销高层,后者刚刚甩掉为其服务30年的代理公司。Harley的首席营销官Mark-Hans Richer说,“很多广告公司都固执认为,他们‘拥有’创意,并能够让创意卖钱。” Victors & Spoils的CCO Evan Fry说,“在Victors & Spoils,你可以了解到事实绝非如此。客户对面坐着个创意总监,他奉上花了几个星期打磨的完美创意,如果你想改动一个字,他就跟你急。这种事情在这儿不会发生。我们的运作模式挺可怕,因为从创意的角度讲,广告圈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感到自己拥有某些别人无法拥有的神奇力量。‘众包’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独特的力量。”
如果客户自己能理清这一团乱麻,他会发现“新世界”大有可为。卡夫公司的合作意向名单里,就收集了近70家新型公司。请注意这不是随便一家什么公司,这是卡夫,美国最大的食品商,每年的营销预算16亿美元。卡夫已经想开,请了GeniusRocket这家新型公司做一个新campaign,重新推出自己的老产品Athenos Hummus豆泥。
GeniusRocket和所有不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公司一样。没有摩天大楼办公室,没有高薪牛b创意人,没有Nobu餐厅的高级寿司晚餐,没有总督酒店为期两星期的拍摄场地。公司只有一个网站(而且还是框架),把TVC先用广播的形式做出来,然后外包到波兰或关岛的某个经过大致认可的“聪明创意人”手里。从前,一个CMO要付给广告公司几百万美元,才能在单点做一个campaign,而如果他交给GeniusRocket,只要4万美元,就能在7个地点做,而且每个点的数据都会被上传到20个网络平台上,以供追踪、测试、敏感度分析和广泛传播。GeniusRocket收取20%-40%佣金,其余部分归“创意人”们所有。卡夫品牌经理Marshall Hyzdu说:“这种搜罗创意的方法貌似更加有趣且划算。传统广告公司想要鹤立鸡群,必须要有大量的日常管理开支。GeniusRocket不同,它只专注于新鲜的创意,这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新模式。”这种想法,让业界人士为之颤抖。Mark Walsh是GeniusRocket创始人之一、现CEO、一个以能够生存在食物链底层为荣的人,他说:“我去拜访了所有那些大公司里的大人物,他们对我的公司几乎没有积极反应。如果老板大于57岁,他会说,‘上帝保佑,我差不多可以离开这行业了。’如果他四十多岁,就要么说‘你是魔鬼,你要来弄死我’,要么说‘你是魔鬼,不过,你能拉我上船吗?别把这事告诉别人’。”
说起数字化世界的无限可能性,Profero数码公司北美区CEO Aaron Reitkopf说,“做广告,没有比这更好的时代,也没有比这更坏的时代。”他一年前辞去Kirshenbaum Bond Senecal + Partners公司CEO的职位,花了一段时间拜访各大广告公司的头头,为自己的下一步做打算。“每次拜访,一开始他们都摆出一副很得志的样子,但当你问他们关于未来该怎么办,他们就会先去把办公室门关上,然后说,‘实话讲,我也不知道。’他们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就是‘太多了’。太多人,太多入错行的人,太多瞎扯的人,太多低效率的人。而这个行业在过去的两年,已经有16万人离开了。嗷,看来要开始大屠杀了。”
[ 出路 ]
想要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存,才是人们来参加Hyper Island这场为期三天的累死人的培训的真正原因。波士顿Hill Holiday的CCO Kevin Moehlenkamp说,“就好像,你进来的时候,并不想承认自己是醉鬼,然而到了第二天,你就会想,也许我真的有一点点、一点点酗酒吧。”他去年秋天就参加了美国区专为广告界顶级创意人设立的课程。“从前,我有点创意精英主义。我以为数字营销只是另外一种媒介而已。” TBWAChiatDay的CCO Rob Schwartz参加了同期课程,他回忆,当时那群精英学员们刚来的时候,都有点装得虚张声势。“每个人都抱臂而坐,气氛很紧张,连笑声也很紧张。那个房间当时有个Twitter转帖,但70%的人不知道Twitter是什么。”
Moehlenkamp和Schwartz说,Hyper Island将广告人从数码旁观者推到了参与者的角色。Schwartz说,“本来,我只是用开放的心态来‘谈论’数字化,但并不觉得置身其中。”他承认自己以前甚至害怕在博客上谈论自己。“在数字化世界特别是社交平台中,你要么还在岸上,要么‘下水’了。参加完这个培训班,我终于‘下水’了。”这个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老家伙开始写博客,说他发现不少数据统计工具,能让他走在别的同事的前面,知道更多实用的互联网真相,而从前很多创意人把理性数据当作创意艺术的大敌。反正,他不希望自己掉队:“我不想被下一轮创意革命淘汰。跟Bernbach比,我还太年轻。我不想被这个时代淘汰。”
很多业内人士都明白,正是这让人眼前一黑的互联网传播,闪烁着各种未知的可能。从业25年的Brian Martin说,“照目前这种状况看来,我们正处在一场创意革命的开端。”广告业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电视广泛普及之时;现在,数字化技术也达到了类似的饱和状态。麦肯的Brien,被赋予让公司起死回生的艰巨任务:“我不明白为啥人们觉得前景凄惨,我觉得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这场变革将会让人们释放前所未有的创意能量。甚至可以说,广告公司快要输给某种未知的创意形式了。”Brien的老板、Interpublic Group的主席和CEO Michael Roth说,“传播界每发生一次变革,我们的客户都需要某种引导。”
IPG旗下Mullen公司的老板Joe Grimaldi,在近三年中都努力尝试在公司中发起改革。Mullen总部在波士顿,是个成立了40多年的传统广告公司,拥有550个员工以及Timberland、LendingTree之类的客户,创意做得还算OK,在业界小有名气。Grimaldi觉得,公司应该抛弃一些陈年陋习,反应更灵敏、更有活力。“我们希望变成一家跨领域的公司,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数字化世界的各种新变化。”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Mullen的CCO Edward Boches说,“我们曾经请外界的人进来,为公司数码化带路,可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总想让公司变成彻头彻尾的数码公司,然后公司里原来那些坚持做品牌策划和大创意的人,就觉得自己被人当成是傻子,是老古董。”这只是问题的开始。“早期,数码传播只是对创意的补充,所以我们都没有认真计算这部分的预算。结果,我们在演绎自己的新角色时,都忽略了专业数码人员的必要性。我们没有针对数字领域来专门打造充分发挥互联网效用的广告,而只是沿着传统传播思维,直接把同样的信息在互联网空间上再说一遍。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白,数字领域的传播方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Mullen懒散地栖居在郊区宫殿一样的豪宅里,员工呆在不同的办公室,被长长的走廊分隔,不同领域的人几乎不产生交集。去年夏天,Grimaldi把公司搬到了波士顿市中心的开放办公室里,让创意人、搞社交媒体的人、搞用户体验的人、媒体策划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混在一起,相互挨着。Boches也把自己CCO“首席创意官”的title改成了更朦胧的CSMO“首席社交媒体官”。Grimaldi正苦恼如何让员工在数码领域产生更多想法,“确实有困难。”
然而,有迹象显示,Grimaldi小有收获。早前,Mullen秉承自己的新守则“对每个试验性的案例都暂时免费”,为奥林巴斯做了一个采用增强现实技术的PEN E-PL1相机广告,人们从网站上下载一张新款相机的图片打印出来,然后把图片对准摄像头,就能看到一个3D效果的相机。这个创意让奥林巴斯年销售增长55%,为Mullen赢得不少大客户,包括Zappos鞋和JetBlue航空公司这两家的社交网络业务,业内同行颇感意外。经济衰退期他们辞退了100名员工,而今年他们有又增添了200个新成员。JetBlue负责市场和营销策略的高级副总裁Marty St. George说,“我们都没想到Mullen会胜出,不过比稿的时候,我们几乎分辨不出他们的创意到底出自在策划那边还是媒体那边,两边的人都极其有默契。”
[ 钱的问题 ]
St George说,JetBlue选择代理公司的过程中,最让人惊异的就是,至今大部分创意人仍然认为30秒tvc是一切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其实这情有可原,因为15%的佣金大部分都是通过给客户拍tvc来获取,对他们来说总是一块肉。这表明广告人还没适应数字时代的真理:从数码传播中获得的利润并不会替代掉传统途径的利润。这个问题也是很多音乐厂牌、出版商、电视台的烦恼。同为IPG旗下的Gotham公司CEO Peter McGuinness也承认,“广告圈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数码传播收费模式,所以更不懂得怎样从中创造利润。”
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广告公司自己造成的。在上世纪80年代,广告公司主要通过兼并的方式,让利润达到最大化。小公司纷纷套现,广告业逐渐变成了四大集团的天下:WPP,Omnicom,IPG和Publicis。结果却事与愿违,“广告公司高层好像比客户的高层赚的钱要多,于是客户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把广告费用降低一点。”
于是服务月费模式成为了主流,广告公司赚到的钱变少了。BMO Capital的Salmon说,“这就像律师行业,费用是根据人头和工作时间来算的。”Grimaldi如此解释月费模式的弊端:“如此一来,广告公司可能为相同的工作增加人数,但这样烧钱反而更快。而且普遍来讲现在钱都没有从前好赚。”客户会聘请采购顾问和成本顾问来为自己压缩广告费用。而且现在谁都没法拥有长期优势,广告公司投入了四个月和1百万美金去比稿,最后还可能是一场空。
疯狂的现状下,广告公司还是会迷恋能赚钱的tvc。The Chaos Scenrio作者、广告界权威人士Bob Garfield说,“广告公司计发明了各种复杂的报酬机制,如果你认真考究每一条收费和媒介花费,就会发现即使是月费制,收费也是随花费而上升的。所以他们总是希望客户在媒介上大方一些。有些公司试图通过革新佣金机制解决问题,却一路跌跌撞撞。”“我们身处一个不懂得如何自保的行业,并不断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才是自己的敌人。” TBWA全球主席Jean Marie Dru在Advertising Age 题为《广告公司身陷报价危机,客户让渐入死亡深渊》宣言中写道。
然而人们仍然抱怨钱赚得不够。广告界CEO们对此设想了2种解决措施:
首先,他们希望报酬与广告实效挂钩。多亏有那些新的数据分析工具,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广告实效。IPG 主席Roth说:“有效的广告报酬多,无效的广告报酬少。遵循这个规则,广告业才能重获良性收益。”这是个不错的想法,问题在于,分析工具并不绝对靠谱:对于Wieden’s为宝洁公司的Old Spice产品发起的那个吸引百万眼球的网络campaign,《广告时代》杂志的推断是,销售飙升主要来自于优惠券部分。
第二种措施,是广告公司一直以来的最大幻想。“我们要去琢磨大创意该如何收费、创意本身的价值如何衡量”,McGuiness说道。所谓大创意,就是像万事达卡那个遍地开花的“无价”campaign一样,毋庸置疑地扭转了整盘生意。奥美前高管、现主管一家创新顾问公司的Brian Collins说,“这是20世纪营销方式的残余物。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能够在那个时代里混得特别好,可惜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Garfield也指出,“在整个大众广告史上,通过广告来创造出巨大财富的成功创意,屈指可数。”他认为,给大创意发薪,是日渐消沉的广告业的最终心愿。“在媒体支出无情萎缩的时代,广告本身就是濒危物种,广告公司摸不找折返的道路,逐渐意识到噩梦将至:广告商业模式将要全然崩溃。”
[ 适者生存 ]
广告公司要为生存而战,首先要与自己作战。全才与专才,互动服务与全代理,传统公司与数码公司之间都正展开激烈的竞赛。这场Forrester Research公司称之为“大比拼”的竞争,其实是在为一块萎缩中的馅饼而殊死斗争,不是人人都能挤进去。为了挤到中心,你必须把别人踩在脚下。Profero公司的Reitkopf说:“有一天我跟一位营销主管聊天,她说:‘我跟同是一家控股公司旗下的促销代理公司、社会营销公司、响应营销公司合作,每次我们一起开会,气氛都很融洽,但一旦我走出会议室喝咖啡,就会有人跟着跑出来,对我说他们可以用更低的价钱,办成和别的公司一样的业务。’”Harley的营销主管Richer补充:“广告公司人际网络本该集合所有专家,为客户出谋划策,但事实上,他们只有在几乎招揽不到生意的时候才这样做。否则,创意机构各自不相干,冷暖自知。他们不是为了解决客户问题而存在的,只是为了摆平各自的账本。”
阳狮集团主席和CEO、法国人Maurice Lévy承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鼓励同一集团下的不同公司相互竞争和超越,是驱动各方增长的最佳方式。现在也有别的控股公司这么干。”
大量控股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把媒介部门从创意部门中划出,成为独立公司,如Omnicom的 OMD 和WPP的Mindshare。此举原意是,即使客户换了别的创意公司,自己仍然能掌握客户的媒介支出。但如今有些营销人,像Johnson & Johnson公司的Brian Perkins,正跪求媒介和创意重新捆绑。Perkins在今年的《广告时代》中写道:“当如今媒介和公关都愈发重要时,为何我们的媒体代理反而从物理上和哲学上都要离创意人愈发的远?”
这道鸿沟,Lévy正在努力消除。他最近创建了Vivaki,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集团内部的媒介机构Starcom MediaVest 和 Zenith Optimedia与数码机构Digitas和Razorfish携手合作。他采用了及其传统的调整财务激励的方式,各分机构仍然自负损益,高层官员的薪金也根据Vivaki下面几家公司的联合损益来计算。去年才加盟阳狮的Razorfish CEO Bob Lord说,“刚开始,这个馒头非常难啃。我的事业从Razorfish起步,我把它的团队打造得超有干劲,发话说我们能为客户解决任何问题。现在,我要说‘好吧,我们客户关系管理方面可能比较弱,但幸好可以让Digitas为我们补充。’这种反差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当然,Lévy和其它控股公司CEO对这种变革试验的决心,源于他们对一站式服务必能战胜分裂式服务的持续信念。IPG集团的Roth在09年收入630万美元,比08年下降40%。他说,“任何领域,任何弯道,我们都必须领先。通过对新型公司投资或与它们合作,把它们变成我们的服务领域之一,才能做到。”换言之,控股公司最终还是干回老本行:搜寻下一个闪光的目标,设法捕获它,让自己原本就很庞大的构造更加庞大。
Rosemarie Ryan 和Ty Montague对未来的期望则比较小。六月前,他俩还是WPP旗下巨头JWT的北美区联合总裁,两人行业经验相加共有40年。后来他们辞职,决定创立一种全无传统传播垃圾和超低工作效率干扰的全新营销业务。他们创建了Co公司,Montague称之为“专为21世纪CEO和CMO而建的品牌工作室”,汇集了广告人、技术人和策略人,能“在正确的时间,调动正确的团队,采取正确的行动,产出正确的结果。”
Co说服了44家专业公司与他们乖乖合作,其中包括Big Spaceship一类的数码公司,还有Victors & Spoils一类的众包公司,甚至有麦肯世界集团,和全美最大的独立媒体服务公司Horizon Media。他们广泛撒网,以此获得强大的增长能力和解决不同领域问题的能力。“我们希望自己尽可能地小,必要时又尽可能地大,” Montague说,“这与规模无关,而与伸缩性有关。即使我们只有五名员工,但我们有1500个能够随机调动的人员。”Horizon的CEO Bill Koenigsberg说,“得到了一单生意,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必须雇一个军队来完成它。这事儿可以给点弹性。”
Co的经营模式,是由客户选择预付佣金 / 支付项目费用 / 产权;对于专业人士的报价,客户不能获得折扣。Montague说:“本质而言,我们是在创立一种不归我们所有的业务。”既然Co本身不拥有任何专业人士,它就注定不会偏好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能够从扎堆的营销队伍中抽离,回到单纯的“帮客户解决问题”上来。要成为Co的客户,必须承诺让Co能与营销高管之外的部门深度沟通。“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也许来自营销部门,但也更可能来自研发、产品创新、设计部门。”
早前,技术观察员Clay Shirky认为“结构复杂的组织趋向崩溃,因为他们不够灵活,当有压力出现,无法迅速回应。”古罗马和玛雅的衰落,正是因为掌权人无法接受更进一步的紧缩和精简。Shirky写道:“经过不断的精简之后,最后一步精简措施,就是瓦解。”他进一步解释:机构解散后,成员会迅速分散,去寻找和尝试新的方式。“如果复杂的东西在行业生态环境中再也难以生存,那么,那些转而去思考如何以简单化的方式解决当下问题的人,而不是熟稔老式复杂方式的人,才能够决定未来。”
如何让走向崩溃的广告行业精简优化、重振旗鼓,Co给我们做了个很好的范例。“小的,才是美好的。”Ryan说。Co是能否成功尚不能定论,但终有让人心驰神往之处,因为不用为某一种可能的未来押上全部的运气。“没有人能明确告诉你未来20年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要么那个人在骗你。”对于业务的增长,Co只有一个计划,就是几位创始人会雇用4-5人的小团队作为帮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以上是行业现状的概览。从去年众多顶级创意人全身而退——CP+B的Bogusky、Saatchi的Gerry Graf、BBH的Kevin Roddy——我们能想象一个全新的广告未来生态,行业新星不断升起,创造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硕果,把反应迟钝的庞大机构远远甩在身后。控股公司仍然存在,但被一群千奇百怪的新公司围攻,这些小公司独立、充满创意、管理费用很低。在未来,行业中的佼佼者更像一只灵活而敏捷的飞鸟(现在的都像一头硕大的恐龙)。它只给最有才华的人提供机会,让其余所有人感到受伤。工作量变大,人力变少,钱更少。然而,这只娇小的飞鸟会凭借自己全新的创造潜力越飞越高,而不会被笨重衰老的身躯拉沉池底。
一名课程教师如此解释:“数码移民的典型行为,就是给别人发了一封email之后,还要打电话过去确认。”
roughly in line with last year’s growth rate of 4
weight loss tipsthe fashion designers fans love to hate